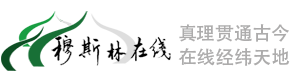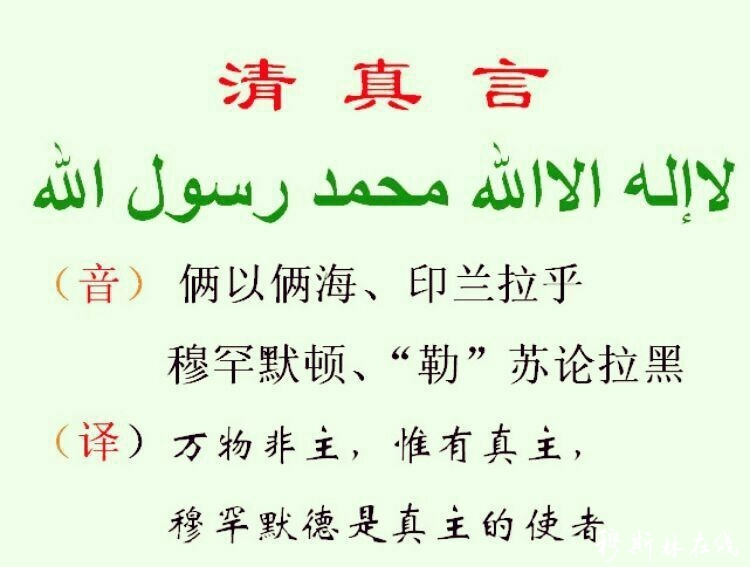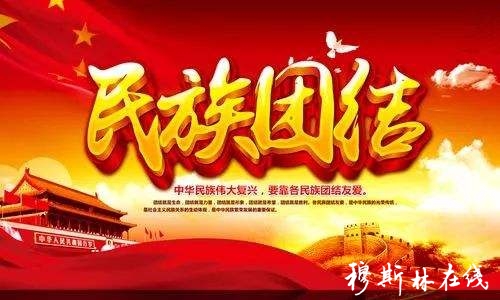在数字时代,宗教的边界已超越寺院、道观、教堂等传统场所,延伸至虚拟的网络公共空间。《宗教教职人员网络行为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的出台,不仅在制度层面明晰了宗教教职人员的网络身份与行为边界,引导其在数字空间中守法合规、正信正行,促使宗教在现代社会实现健康传承与自我净化,通过法治化路径平衡宗教信仰自由与社会秩序,既维护了信众的合法权益,也为营造清朗的网络生态、巩固社会和谐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以纲明目
我国宗教事务治理始终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基本原则。《规范》旨在为宗教教职人员的网络行为确立制度准则与行为纲领,从而维护互联网宗教领域的良性秩序,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规范》并非孤立的文件,而是我国宗教事务治理体系在数字时代的有机延展。一方面,它重申了《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既有规章的法治精神与底线要求;另一方面,又在网络新场景下,对行为主体的身份界定、行为边界的划定以及责任归属的认定进行了针对性细化与补充,体现出我国宗教事务治理从传统空间向数字空间延伸的制度自觉与法治理性。
顾名思义,《规范》所指向的对象,是“依法取得宗教教职人员资格、可以从事宗教教务活动的人员”,且宗教教职人员资格的取得应当经由宗教团体认定,并报宗教事务部门备案。这意味着,宗教教职人员身份是一种经过法定程序确认的社会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舆论中有声音担忧《规范》难以约束假和尚、假道士等假冒教职人员之人。事实上,相关法规早已对此作出回应。2022年施行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在互联网上假冒宗教教职人员开展活动,均属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应予以查处。由此可见,《规范》与既有法规形成联动与互补,共同织密宗教事务治理的制度之网。
《规范》的宗旨不在禁,而在导;不在否定宗教的网络存在,而在确立可识别的主体、可区分的受众与可追责的程序。《规范》第四、第五条对此作出了具体规定:宗教教职人员不以宗教教职人员身份实施网络行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宗教事务管理有关规定;以宗教教职人员身份注册、使用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类网络公众账号,应当向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提交宗教教职人员证书供核验。同时明确:宗教教职人员在互联网上讲经讲道或者从事宗教教育培训,可以且仅限于通过取得《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的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寺观教堂依法自建的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等进行。
宗教身份认证与特定平台准入的“双重门槛”,在制度层面起到了双向规范的作用:一方面,为宗教教职人员在教内进行信仰交流提供了合法、清朗的表达空间,使宗教在法治轨道内健康延续;另一方面,推动公共平台建立内容分级与审核机制,从源头上防止“场所不当”“对象不当”的网络传教行为。如此,私人表达与宗教表达的渠道得以分明,信仰之语与公共话语的边界也愈加清晰,从而为数字时代的宗教表达确立了一种有序而温和的制度框架。
二、以规净教
《规范》的施行,是顺应网络时代之变与宗教事务治理新形势的必然要求。这既是全面从严治教的关键举措,也是宗教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制度契机,防止网络空间的浮躁与歪风侵蚀宗教,从而保障宗教健康传承。通过系统化与针对性的条文设计,《规范》以法治方式回应了当前互联网宗教领域存在的乱象与风险,并将“治之以理、约之以法”的要求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层面。
首先,《规范》倡导宗教教职人员要培养良好的网络习惯,自觉抵制不良网络文化,杜绝以宗教话题博取流量、追逐热点的倾向。《规范》通过法治化的方式,为宗教伦理筑起制度防线,使信仰免于被低俗化、娱乐化、资本化的网络内容所侵蚀,保护了信教公民的正当信仰权益。
其次,《规范》着眼于国家安全与文化安全两大维度,重申了互联网宗教领域行为的政治与法律底线。
宗教教职人员不得借助网络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不得以宗教之名干预司法、教育、婚姻及社会管理等国家制度;更不得通过互联网与境外势力勾连,支持或参与任何形式的宗教渗透活动。这不仅是对宗教领域政治纪律的制度化明晰,更是防范宗教被异化为社会动员、群体对立或意识形态渗透工具的前瞻性设计。《规范》以法治的方式划定了宗教活动与社会秩序的合理边界,维护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与思想文化领域的清朗。
再次,《规范》严禁宗教教职人员宣扬异端邪说、附佛外道,亦禁止其以打卦、占卜、算命等封建迷信行为损害宗教形象与社会理性。在此意义上,既是防范宗教失范的制度防线,也是守护理性精神与文明秩序的重要屏障。
三、以制清网
2016年起,由中央网信办牵头、多部门协同推进的“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持续以整治互联网乱象、净化网络空间为核心目标。《规范》的出台正是这一系统性治理格局中的关键一环,其根本旨趣在于优化数字时代的网络生态,推动公共舆论空间的理性化与秩序化。
例如,《规范》在未成年人保护原则中明确规定:宗教教职人员不得通过网络向未成年人传播灌输宗教思想、诱导信教,或者组织未成年人参加涉宗教教育培训、夏(冬)令营等,或者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此举以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为界限,特别区分宗教传承与教育启蒙,既防止青少年因过早接触宗教观念而形成认知缺陷与心理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社会对宗教界可能产生的误解与道德疑虑。
与此同时,面对AI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规范》规定:宗教教职人员应当依法规范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不得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传教,制作、发布、传播违法信息或者从事违法违规活动。《规范》通过明确宗教教职人员的可追溯责任边界,促使其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保持理性与慎思。
此外,为防止宗教议题被滥用于制造对立或激化社会情绪,《规范》明确要求:宗教教职人员不得通过网络发布未经核实的虚假信息;不得挑拨是非、制造对立、制谣传谣、诬告陷害、攻击诽谤等,破坏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内部和睦相处,歧视、侮辱信教公民或者不信教公民。这一规定不仅旨在维护公民人格与名誉权的正当边界,更在宏观层面上维护宗教和谐、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使宗教活动回归其精神本位与公共伦理秩序之中。
综上所述,于宗教界而言,《规范》可视为一条守护信仰纯正与秩序稳定的“护城河”。《规范》的落实,不仅为依法开展宗教活动提供了稳定而合法的制度保障,也在无形之中重塑了宗教界的社会声誉与公共形象,使信仰的庄严与理性得以在数字时代健康传承。
于社会公众而言,《规范》则构筑了一张防范风险、守护安全的“防护网”。《规范》使公众在接触互联网宗教信息时能够更清晰地行使知情权,从而作出理性的判断。
(作者何欢欢为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胡雨竹为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数字时代,宗教的边界已超越寺院、道观、教堂等传统场所,延伸至虚拟的网络公共空间。《宗教教职人员网络行为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的出台,不仅在制度层面明晰了宗教教职人员的网络身份与行为边界,引导其在数字空间中守法合规、正信正行,促使宗教在现代社会实现健康传承与自我净化,通过法治化路径平衡宗教信仰自由与社会秩序,既维护了信众的合法权益,也为营造清朗的网络生态、巩固社会和谐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以纲明目
我国宗教事务治理始终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基本原则。《规范》旨在为宗教教职人员的网络行为确立制度准则与行为纲领,从而维护互联网宗教领域的良性秩序,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规范》并非孤立的文件,而是我国宗教事务治理体系在数字时代的有机延展。一方面,它重申了《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办法》《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既有规章的法治精神与底线要求;另一方面,又在网络新场景下,对行为主体的身份界定、行为边界的划定以及责任归属的认定进行了针对性细化与补充,体现出我国宗教事务治理从传统空间向数字空间延伸的制度自觉与法治理性。
顾名思义,《规范》所指向的对象,是“依法取得宗教教职人员资格、可以从事宗教教务活动的人员”,且宗教教职人员资格的取得应当经由宗教团体认定,并报宗教事务部门备案。这意味着,宗教教职人员身份是一种经过法定程序确认的社会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舆论中有声音担忧《规范》难以约束假和尚、假道士等假冒教职人员之人。事实上,相关法规早已对此作出回应。2022年施行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任何个人在互联网上假冒宗教教职人员开展活动,均属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应予以查处。由此可见,《规范》与既有法规形成联动与互补,共同织密宗教事务治理的制度之网。
《规范》的宗旨不在禁,而在导;不在否定宗教的网络存在,而在确立可识别的主体、可区分的受众与可追责的程序。《规范》第四、第五条对此作出了具体规定:宗教教职人员不以宗教教职人员身份实施网络行为,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宗教事务管理有关规定;以宗教教职人员身份注册、使用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类网络公众账号,应当向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提交宗教教职人员证书供核验。同时明确:宗教教职人员在互联网上讲经讲道或者从事宗教教育培训,可以且仅限于通过取得《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的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寺观教堂依法自建的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等进行。
宗教身份认证与特定平台准入的“双重门槛”,在制度层面起到了双向规范的作用:一方面,为宗教教职人员在教内进行信仰交流提供了合法、清朗的表达空间,使宗教在法治轨道内健康延续;另一方面,推动公共平台建立内容分级与审核机制,从源头上防止“场所不当”“对象不当”的网络传教行为。如此,私人表达与宗教表达的渠道得以分明,信仰之语与公共话语的边界也愈加清晰,从而为数字时代的宗教表达确立了一种有序而温和的制度框架。
二、以规净教
《规范》的施行,是顺应网络时代之变与宗教事务治理新形势的必然要求。这既是全面从严治教的关键举措,也是宗教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制度契机,防止网络空间的浮躁与歪风侵蚀宗教,从而保障宗教健康传承。通过系统化与针对性的条文设计,《规范》以法治方式回应了当前互联网宗教领域存在的乱象与风险,并将“治之以理、约之以法”的要求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层面。
首先,《规范》倡导宗教教职人员要培养良好的网络习惯,自觉抵制不良网络文化,杜绝以宗教话题博取流量、追逐热点的倾向。《规范》通过法治化的方式,为宗教伦理筑起制度防线,使信仰免于被低俗化、娱乐化、资本化的网络内容所侵蚀,保护了信教公民的正当信仰权益。
其次,《规范》着眼于国家安全与文化安全两大维度,重申了互联网宗教领域行为的政治与法律底线。
宗教教职人员不得借助网络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不得以宗教之名干预司法、教育、婚姻及社会管理等国家制度;更不得通过互联网与境外势力勾连,支持或参与任何形式的宗教渗透活动。这不仅是对宗教领域政治纪律的制度化明晰,更是防范宗教被异化为社会动员、群体对立或意识形态渗透工具的前瞻性设计。《规范》以法治的方式划定了宗教活动与社会秩序的合理边界,维护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与思想文化领域的清朗。
再次,《规范》严禁宗教教职人员宣扬异端邪说、附佛外道,亦禁止其以打卦、占卜、算命等封建迷信行为损害宗教形象与社会理性。在此意义上,既是防范宗教失范的制度防线,也是守护理性精神与文明秩序的重要屏障。
三、以制清网
2016年起,由中央网信办牵头、多部门协同推进的“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持续以整治互联网乱象、净化网络空间为核心目标。《规范》的出台正是这一系统性治理格局中的关键一环,其根本旨趣在于优化数字时代的网络生态,推动公共舆论空间的理性化与秩序化。
例如,《规范》在未成年人保护原则中明确规定:宗教教职人员不得通过网络向未成年人传播灌输宗教思想、诱导信教,或者组织未成年人参加涉宗教教育培训、夏(冬)令营等,或者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此举以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为界限,特别区分宗教传承与教育启蒙,既防止青少年因过早接触宗教观念而形成认知缺陷与心理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社会对宗教界可能产生的误解与道德疑虑。
与此同时,面对AI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规范》规定:宗教教职人员应当依法规范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不得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传教,制作、发布、传播违法信息或者从事违法违规活动。《规范》通过明确宗教教职人员的可追溯责任边界,促使其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保持理性与慎思。
此外,为防止宗教议题被滥用于制造对立或激化社会情绪,《规范》明确要求:宗教教职人员不得通过网络发布未经核实的虚假信息;不得挑拨是非、制造对立、制谣传谣、诬告陷害、攻击诽谤等,破坏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内部和睦相处,歧视、侮辱信教公民或者不信教公民。这一规定不仅旨在维护公民人格与名誉权的正当边界,更在宏观层面上维护宗教和谐、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使宗教活动回归其精神本位与公共伦理秩序之中。
综上所述,于宗教界而言,《规范》可视为一条守护信仰纯正与秩序稳定的“护城河”。《规范》的落实,不仅为依法开展宗教活动提供了稳定而合法的制度保障,也在无形之中重塑了宗教界的社会声誉与公共形象,使信仰的庄严与理性得以在数字时代健康传承。
于社会公众而言,《规范》则构筑了一张防范风险、守护安全的“防护网”。《规范》使公众在接触互联网宗教信息时能够更清晰地行使知情权,从而作出理性的判断。
(作者何欢欢为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胡雨竹为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中国宗教》杂志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