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 情 深
——献身伊斯兰的社会活动家马天英 ——
达慧中
哈志·依布拉欣·马天英先生(1900—1982年)是我国著名的回族社会活动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在中华民族觉醒的大潮中,他成为振兴回族的中坚力量,表现出毫不畏惧、勇往直前的精神。1932年在回族的护教运动中,他作为上海护教团的三成员之一,代表上海穆斯林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南京政府迫于全国穆斯林斗争的压力,颁布明令声言政府爱护回民,维护宗教,勒令侮辱宗教的刊物停刊,惩办撰稿人等决定。这一护教活动,维护了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尊严,已载入了回族和伊斯兰教史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与国民外交,先后倡导并参加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和南洋访问团,赴伊斯兰教国家进行抗日宣传,取得显著成绩。战后,曾先后担任埃及驻开罗公使馆二等秘书和驻马来亚领事馆总领事。1949年以后,在马来西亚定居,将全部身心献给了伊斯兰教事业,由于他对国家和国际事务以及宗教方面的卓越贡献,曾先后荣获中国、法国、尼泊尔、埃及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奖章和勋章。
马天英先生是笔者的舅父,他为国、为教,竭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现在仍有一些老人怀念他,但对他离国后的几十年经历,不甚了解,今日之年轻人更不知我国回族当中有这样一位人物,曾在二十世纪中,为多难的祖国做出过贡献,同时赢得了世界穆斯林的尊敬。笔者根据艾骊马琳女士著《马天英传》、薛文波先生著《雪岭重泽》和笔者母亲的回忆,写就了以下几段往事,以飨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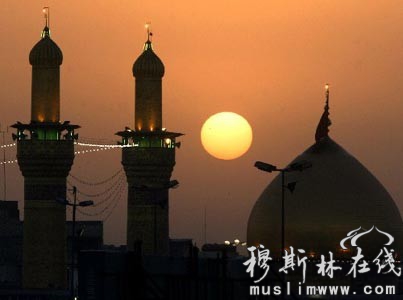
雏 鹰 展 翅
从十九世纪中叶,清王朝伴随着封建社会的丧钟开始走向末路,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民众更是苦不堪言,回族群众多数人只能靠经营小买卖为生。
马天英先生正是生于世纪之交的1900年,是山东临清馀庆堂马家武状元的后代。他的祖父为了躲避战乱,在他出生的四、五十年前举家逃往北平,父亲因为没有太多文化,也只能靠做小买卖度日。家境贫寒,每到年关,父亲往往为躲债而逃出家门。有一次,高利贷债主在端午节为逼债用剪刀刺伤了他的母亲,只有十一岁的马天英无法忍受父母为生活付出了血的代价,他痛恨债主的凶残,也为挣脱贫困生活的羁绊而求索。听他的同学说宣武门内的天主教堂里有一所法文学堂,他向往到这所洋学堂去求学,望想将来不再像父亲那样过穷日子。可是那样的学堂一学期就收四十个大银元,在那里读书的大多是富家子弟,高昂的学费让他望而却步,几经犹豫之后,他还是战战兢兢地对父亲说了自己的愿望。
马天英的父亲虽然识字不多,但有远见卓识,他常开玩笑地说:“我要是读过书,也能当个朝廷二品大员。”在父亲高大魁梧身体里,流淌着先祖武状元的血液,英俊的脸庞上,窝眼、隆鼻,透着睿智而干练,他了解自己的儿子年纪虽小却有大志向;也相信自己的儿子不是心血来潮说一说玩儿的。他父亲只问了他一句话:“法文学校你觉得你能念下来吗?”他说:“要是念,死也要念下来!只是钱……。”父亲说:“钱的事你就甭管了。”他哪里知道父亲一咬牙卖掉了自己的御寒的皮袄和母亲的首饰,决心供他去读洋文。
家贫出孝子,马天英年仅十一、二岁,就开始替父亲分担生活的重担。有一次,父亲和羊肉批发商发生争执,他不忍心让父亲再看这些人的白眼,从此,他除了到洋学堂去学法文以外,还要承担去批发羊肉的任务。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轻声把他唤醒,他睁开惺忪的睡眼,心中记起了自己要替父亲去买羊肉,猛地跳下了床,立刻用冰冷的水激一下脸,使自己顿时清醒过来,急急忙忙奔出家门。炎热的夏季,酷暑难耐,百斤重的羊肉,使他汗流浃背,小小年纪的他,开始品尝生活的艰辛。冬季来临,滴水成冰,呼啸的北风打透了他又薄又旧的小棉袄。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集聚着对父母的爱和对家庭的责任感,即使是再重的负担和再远的路程,也难以使他屈服,汗水湿透了衣衫,刺骨的寒风袭来,不知道是冷还是热,他就是这样踏入了人生之路。
在二十年代初,中国人有几个人知道洋文为何物的?小小的天英哪里懂得法文的厉害:法文文法和中文完全不同,什么都有阴阳,桌椅是阴,黑板粉笔是阳,手是阴,手指是阳,个个动词跟着人称的不同没完的变化,真把人搅昏了头。发音又是那么晦涩难念,舌头像不会打弯儿,在课堂上真是如坐针毡。他坐在后排,个子又小,看不见老师和黑板,他向老师要求让他坐在前排,老师说:“不行,座位是根据学习成绩排列的,你现在的成绩只能坐在这个位置上。”几个星期学下来,法文老师玛利小姐对他说:“你虽然不迟到、不早退,学习也很认真,但是有的人舌头太硬,不适合学习外语,我看你还是不要浪费你父亲的钱了……。”他听到老师的话,像头上遭到了沉重的一击,想起父亲交到他手中那包白花花的银元,犹如压在他心头的千斤重石,他用渴求的眼神望着玛利小姐说:“不!不!请您再等等,我再试试,再试试。”马天英从小就性格倔强,从不服输,他想:他们能行,我也能行!
他开始向法文宣战,无论是上学、下学,还是在行走的路上,他不停地念,不停地记,甚至在睡梦里也在朗读法文,他把整个的身心都融化在法文里。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月的努力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他终于跻身优秀学生的第一排座位上。
1917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作为参战国,派去了众多华工,此时法国和比利时人来华遴选能够带领华工的懂法语的人才。
一位名叫毛理士·白的法国人看着学校里挑选出的学生,一个面色红润,英姿勃发的少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了解了这个少年的情况,对他说:“马先生,我很相信你的人品,可惜你太小了,你究竟有多大?”
他说:“我十七岁,按你们外国人算实足年龄,应该是十六岁。”
白先生皱着眉头说:“你太小了,你能命令人吗?别人能服从你的命令吗?”
马天英昂首挺胸,毫不犹豫地说:“先生,如果我能接受命令,服从别人,我就能发号施令,叫别人服从我!”
“说得好!”白先生不由得赞叹道,但是他又说:“不过,我看你还是太小了,一看就是个孩子样儿,那些二、三十岁的华工恐怕不会听你的。”
“先生,你是嫌我个子还没有长足吗?个子高底、年龄大小与能力并没有多大关系,你们以前的皇上拿破仑也是小个子,比我还矮呢。他却能叱咤风云,鞭打整个欧洲,为法国写下煊赫历史。”马天英侃侃而谈,早已忘记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位高傲的法国人。“一个人不是以他的身材的高低大小来估量他的才干,如果你怀疑我是否有能力令人宾服,那我保证,我能够!我读书很多,可以用我的知识说服人,用我的诚挚感动人,用我的言行为别人做出榜样,我有强壮的身体,能背负百斤,行几十里路而不觉疲倦。我有清醒的头脑,能分析问题…….”白先生边听边露出了笑容,满意地点头,对校长说:“我们就挑选他!”他拍拍马天英的肩膀说:“好,小伙子,我选你做领队,相信你会好好干出成绩的,祝你好运,再会!”
马天英的脸上绽开欣喜的笑容,父亲含辛茹苦的培育,自己六年的寒窗苦读,终于迎来了报效家、国的机会。
但是,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少年,真要离开家,哪里割舍得了骨肉亲情,走出熟习而破旧的家门,望着日夜为他操劳的母亲和她充满泪水的双眼,他久久不忍离去,多么想再多看亲人一眼,最后他十分不忍心地对母亲说:“妈,我倒着走吧!”
新生活在召唤!他心中充满了希望,犹如一支羽毛未丰的雏鹰,向往湛蓝的天空,他将要展开稚嫩的双翅,鹏程万里,越过波涛汹涌的大海,飞向神秘的国度。
上一篇:古河州走出的新闻发言人
下一篇:穆罕默德·阿里·冯福宽
- • ·近代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四大阿訇之哈德成阿訇(2010-06-04)
- • ·近代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四大阿訇之王静斋阿訇(2010-06-04)
- • ·近代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四大阿訇之达浦生阿訇(2010-06-04)
- • ·近代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四大阿訇之马松亭阿訇(2010-06-04)
- • ·纪念伊斯兰教育家——艾哈迈德·阿萨勒博士(2010-0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