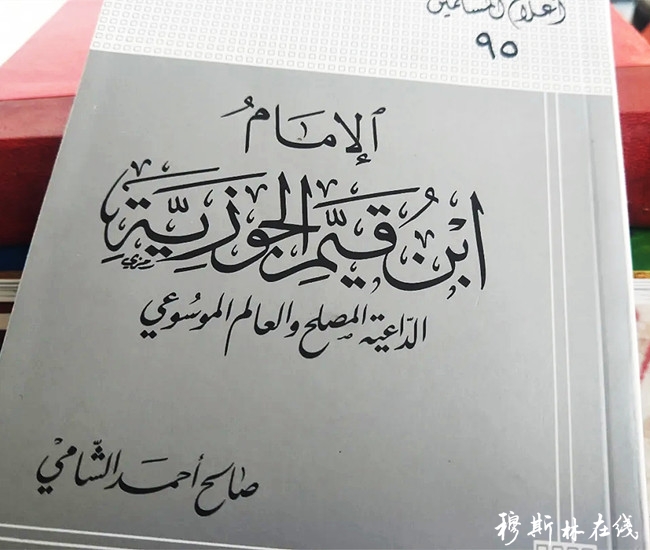-
马明良,留学回国人员,西北民族大学西北 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中心主任、伊斯兰文化研 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甘肃省伊斯兰教协 会副会长 [详细]
-
安优布·丁士仁,男,回族,博士,1966年 10月5日出生于甘肃省临潭县,现任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 生导师 [详细]
-
张维真,回族,甘肃临夏人。中国著名的穆 斯林学者。 1963年生于甘肃临夏(河州)。 1982—1985年,在临夏外国语学校(原中阿 学校)学习。 [详细]
-
优素福·格尔达威(1926.9.9-- ),阿文: يوسف القرضاوي ,是当代最突出的伊斯兰百 科式大学者,爱资哈尔大学博士,世界穆斯 林学者联盟主席 [详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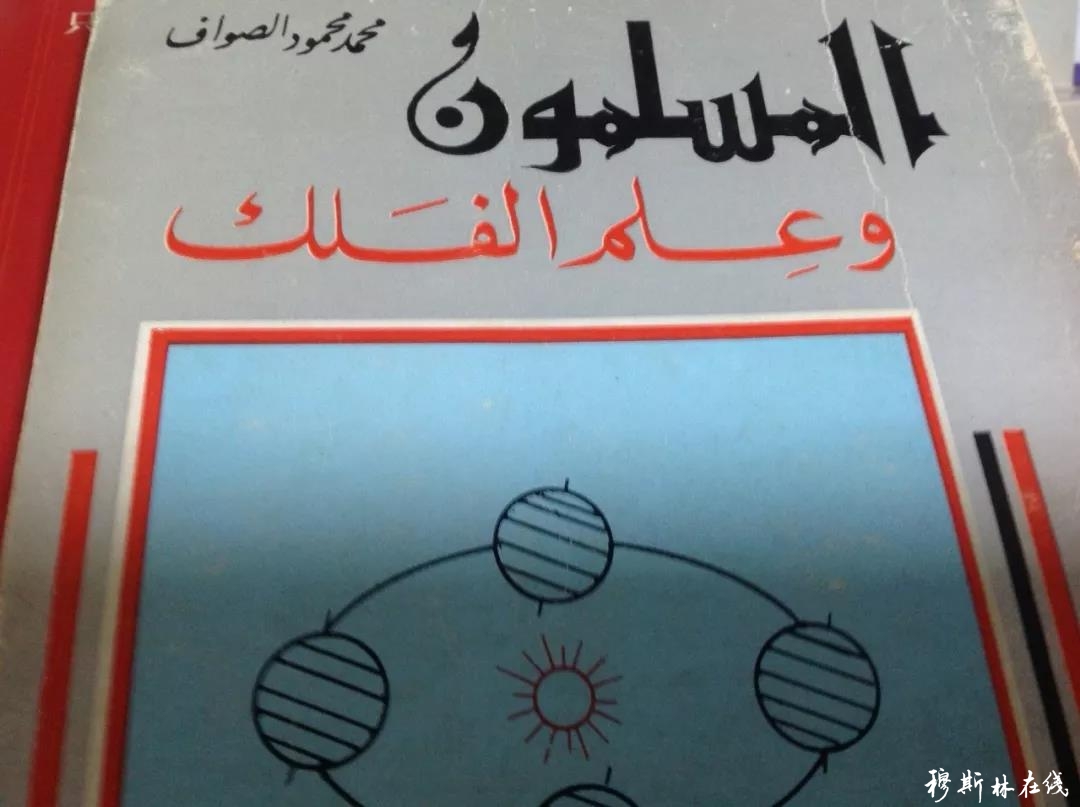 纵观《穆斯林与天文学》,作者萨瓦夫以无可辩驳的历史和经典事实否定了那位谢赫的观点,但不失一位学者应有的温和、包容与大度,与一些固执字面的人抨击他人时的尖刻、诽谤与诋毁形成对照。《穆斯林与天文学》,让我们学到穆斯林的辉煌历史、经训与科学一致的同时,也让我们学到一种就事论事、尊重他人、批评有度的治学态度。
纵观《穆斯林与天文学》,作者萨瓦夫以无可辩驳的历史和经典事实否定了那位谢赫的观点,但不失一位学者应有的温和、包容与大度,与一些固执字面的人抨击他人时的尖刻、诽谤与诋毁形成对照。《穆斯林与天文学》,让我们学到穆斯林的辉煌历史、经训与科学一致的同时,也让我们学到一种就事论事、尊重他人、批评有度的治学态度。 -
 根据先贤、伊玛目、学者们的认定,公认的教法依据是四个:古兰经الكتاب、圣训السنة、公决الإجماع和类比القياس。此外,还有一些内容,是否教法依据,学者们颇有分歧,如律例照旧الاستصحاب、择善而从(有人译为唯美) الاستحسان 、圣门弟子的观点قول الصحابة、前人的教法شرع من قبلنا、酌定利益المصالح المرسلة ,等等。至于其他内容,包括灵感、洞见、睡梦等,权威伊玛目、学者们没有把它们列入教法依据,因此几乎所有法源学著作中涉及教法依据时,提到上述公认的教法依据以及有分歧的教法依据,却只字不提灵感、洞见和睡梦。
根据先贤、伊玛目、学者们的认定,公认的教法依据是四个:古兰经الكتاب、圣训السنة、公决الإجماع和类比القياس。此外,还有一些内容,是否教法依据,学者们颇有分歧,如律例照旧الاستصحاب、择善而从(有人译为唯美) الاستحسان 、圣门弟子的观点قول الصحابة、前人的教法شرع من قبلنا、酌定利益المصالح المرسلة ,等等。至于其他内容,包括灵感、洞见、睡梦等,权威伊玛目、学者们没有把它们列入教法依据,因此几乎所有法源学著作中涉及教法依据时,提到上述公认的教法依据以及有分歧的教法依据,却只字不提灵感、洞见和睡梦。 -
 对于逝者,不要苛薄一种信仰、一种文化对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影响往往是根深蒂固的。比如对不在场的人,说他(或她)的坏话,在穆斯林的文化
对于逝者,不要苛薄一种信仰、一种文化对一个民族整体素质的影响往往是根深蒂固的。比如对不在场的人,说他(或她)的坏话,在穆斯林的文化 -
 中国共产党历来尊重我国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当年红军长征路过回族聚居区时,毛主席、朱总司令特别强调尊重回族的习俗,不准把猪肉带进清真寺,并对违反这一规定的人严肃处理;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回民支队准许有随军阿訇,乃是基于对民族信仰、民族文化的尊重;毛泽东为延安清真寺亲笔题写“清真寺”,该匾一直保留至今,是对穆斯林的信仰给予尊重和保护的历史见证;中共中央早在延安时期就指示撰写《回回民族问题》,不仅提到尊重回回民族的文化传统,而且指出“伊斯兰教不只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还包括着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解放兰州时,彭德怀将军特意指示派军队保护清真寺,不得侵犯,等等。
中国共产党历来尊重我国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当年红军长征路过回族聚居区时,毛主席、朱总司令特别强调尊重回族的习俗,不准把猪肉带进清真寺,并对违反这一规定的人严肃处理;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下的回民支队准许有随军阿訇,乃是基于对民族信仰、民族文化的尊重;毛泽东为延安清真寺亲笔题写“清真寺”,该匾一直保留至今,是对穆斯林的信仰给予尊重和保护的历史见证;中共中央早在延安时期就指示撰写《回回民族问题》,不仅提到尊重回回民族的文化传统,而且指出“伊斯兰教不只是一种宗教信仰”,而且“还包括着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解放兰州时,彭德怀将军特意指示派军队保护清真寺,不得侵犯,等等。 -
世界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舞台,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在多样性中也有同一性。我们在尊重各宗教之异的同时,也要尽力求各宗教之同,寻找全人类公认的普世伦理和共同价值观,为构建一个既有特殊性,又有共性,既有多样性,也有同一性的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和而不同”世界文明而努力。
-
 作为传统经典,《沙米》固然不乏参考价值,它的历史地位也不容小觑。但除了古兰经、可靠的圣训,任何著作可对可错,就像除了先知,任何人可对可错一样。我们的弊端往往是,要么画地为牢,把传统经典与古兰经、圣训相提并论,甚至超越后者,做盲从主义;要么否定传统,另起炉灶,从而抹杀前辈伊玛目、学者既有的贡献。正确的做法,便是如大贤阿里所说,“用真理衡量人,而不是用人衡量真理。”
作为传统经典,《沙米》固然不乏参考价值,它的历史地位也不容小觑。但除了古兰经、可靠的圣训,任何著作可对可错,就像除了先知,任何人可对可错一样。我们的弊端往往是,要么画地为牢,把传统经典与古兰经、圣训相提并论,甚至超越后者,做盲从主义;要么否定传统,另起炉灶,从而抹杀前辈伊玛目、学者既有的贡献。正确的做法,便是如大贤阿里所说,“用真理衡量人,而不是用人衡量真理。” -
如果穆斯林不学习教门知识,其结果便是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并在自己的宗教中标新立异,脱离教法规定,自以为是地崇拜真主。但真主的确无求于那些标新立异者的崇拜。因为真主是立法者,这些标新立异者没有给伊斯兰立法的权利。他们的所作所为既没有获得真主的允许,也没有获得穆圣的许可。穆圣说:“谁做了一件我所未成命令过的事,那他已经背叛。”穆圣还说:“你们务必要提防(宗教中的)新生的事物,因为(宗教中的)每一个新生异端都是迷误。”
-
 然而,当穆斯林由于偏离伊斯兰而走向全面衰落的时候,他们在自己的宗教生活中几乎完全放弃了这一生活常识,丢开西瓜,攥紧芝麻,并为自己的这一举动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假如他们把自己宗教生活中的这些选择运用到自己日常生活的游戏规则中,他们必然觉得幼稚可笑、匪夷所思。
然而,当穆斯林由于偏离伊斯兰而走向全面衰落的时候,他们在自己的宗教生活中几乎完全放弃了这一生活常识,丢开西瓜,攥紧芝麻,并为自己的这一举动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假如他们把自己宗教生活中的这些选择运用到自己日常生活的游戏规则中,他们必然觉得幼稚可笑、匪夷所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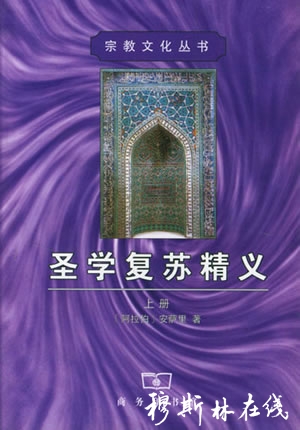 我认为,安萨里与伊本 鲁士德之间的“胜负”问题似乎也应从客观、现实、不掺个人愿望的层次去评定,而不是先入为主、一厢情愿式地加以主观臆断。安萨里及其著作在伊斯兰世界深入人心,近千年而不衰;伊本 鲁士德的哲学著作只是被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而见于某些图书馆。在今天的伊斯兰世界,当你提到伊本 鲁士德时,民间几乎无人知晓,而安萨里及其思想却是有口皆碑,人人皆知。这一事实不是比理论更能说明问题吗?
我认为,安萨里与伊本 鲁士德之间的“胜负”问题似乎也应从客观、现实、不掺个人愿望的层次去评定,而不是先入为主、一厢情愿式地加以主观臆断。安萨里及其著作在伊斯兰世界深入人心,近千年而不衰;伊本 鲁士德的哲学著作只是被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而见于某些图书馆。在今天的伊斯兰世界,当你提到伊本 鲁士德时,民间几乎无人知晓,而安萨里及其思想却是有口皆碑,人人皆知。这一事实不是比理论更能说明问题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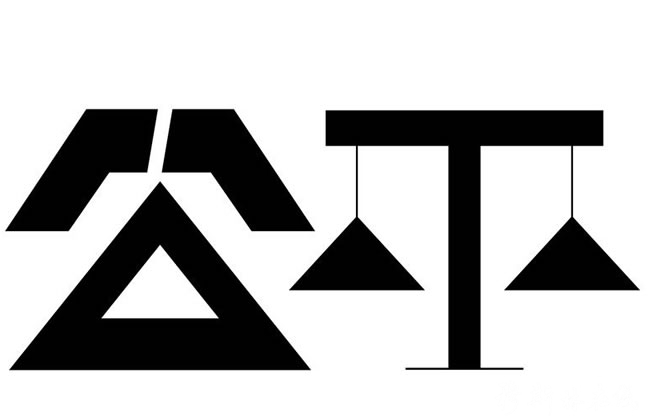 诚然,人世间没有绝对的公平,绝对的公平属于真主,但人们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可以达到相对的公平。不然,一个者麻提、一个社区、一个社会,就会霸道、不义和种种罪恶盛行,人们在善恶面前,失去原则,对正义与非正义,麻木不仁,只问利害,不问是非,甚至会同流合污,助纣为虐,受害者越来越多,他们会愤愤不平,不平则鸣,有的甚至会心理失衡,情绪失控,通过正常渠道得不到解决,必然会走向失望甚至绝望,而绝望的人们会走向极端,会寻求不正当手段解决正当的诉求,其后果不堪设想。
诚然,人世间没有绝对的公平,绝对的公平属于真主,但人们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可以达到相对的公平。不然,一个者麻提、一个社区、一个社会,就会霸道、不义和种种罪恶盛行,人们在善恶面前,失去原则,对正义与非正义,麻木不仁,只问利害,不问是非,甚至会同流合污,助纣为虐,受害者越来越多,他们会愤愤不平,不平则鸣,有的甚至会心理失衡,情绪失控,通过正常渠道得不到解决,必然会走向失望甚至绝望,而绝望的人们会走向极端,会寻求不正当手段解决正当的诉求,其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