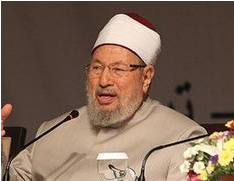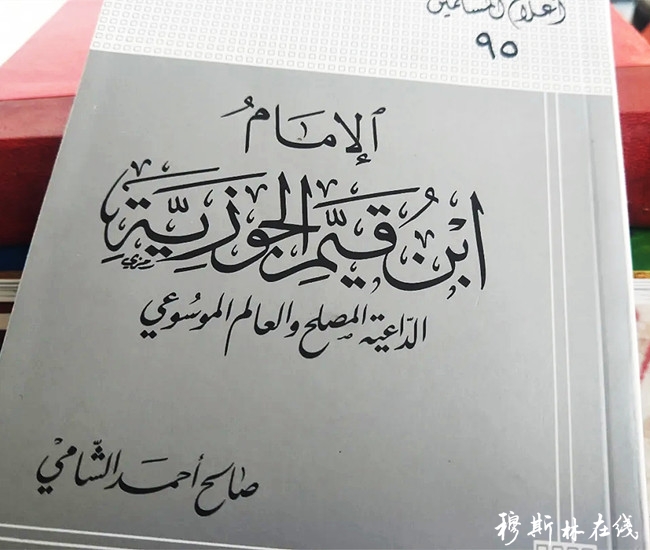-
马明良,留学回国人员,西北民族大学西北 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中心主任、伊斯兰文化研 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甘肃省伊斯兰教协 会副会长 [详细]
-
安优布·丁士仁,男,回族,博士,1966年 10月5日出生于甘肃省临潭县,现任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外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 生导师 [详细]
-
张维真,回族,甘肃临夏人。中国著名的穆 斯林学者。 1963年生于甘肃临夏(河州)。 1982—1985年,在临夏外国语学校(原中阿 学校)学习。 [详细]
-
优素福·格尔达威(1926.9.9-- ),阿文: يوسف القرضاوي ,是当代最突出的伊斯兰百 科式大学者,爱资哈尔大学博士,世界穆斯 林学者联盟主席 [详细]
-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倾向来看,伊本·赫尔东( 1332 —1406 )堪称是伊本·泰米叶维新、演绎思想的延伸。而且,他在许多学术领域汲取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比如,伊本·赫尔东不采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而是注重实际考察和研究;批判“理念说”、“流溢说”等形而上学,抨击整个希腊哲学及受它影响的阿拉伯哲学,认为它既无裨于今生,又无益于后世,而是诉诸于源自伊斯兰沙里亚的实验主义研究。
-
曾几何时,“解放”一词似乎与宗教扯不上边,因为在现代许多人那里,宗教是“对人间痛苦的虚幻的反应”,是“人民的鸦片”,它只与“飘渺”、“麻醉”、“迷信”等词联系在一起,而与作为进步、先进和文明的“解放”有何关系呢?
-
据传,伊玛目莎菲仪说过:“假如没有忘记,人人可以成为学者。”一般而言,伊玛目的这句话没错,忘记的确是学习的大敌。君不见,中国古代和阿拉伯古代,不都在讴歌那些“过目不忘”的学者吗?然而,绝对不忘,未必是一件好事。许多情况下,人需要忘记,而且必须忘记。人有失落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伤感的时候,有一蹶不振的时候。人生本是坎坎坷坷,崎岖不平,没有哪个人会一直一帆风顺,没有烦恼。
-
伊斯兰初期的一些首创性学科,对后来许多学科和知识的开发和繁荣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的一个显学便是圣训学。圣训即先知的语言、行为、属性及先知所默认的言行。实际上,对圣训的收集和整理可追溯到先知时代。为避免人们把古兰经与圣训混淆起来,先知初期禁止圣门弟子记录圣训,后来又允许记录,而圣训的口头传述却从未中断。由于古兰经指示穆斯林学习和仿效先知,先知去世后穆斯林遇到许多新的难题,在一些问题的看法出现了分歧,如对先知继承人问题、对某段古兰经的不同解释、在古兰经中没有发现对某一律例的断法,等等,所以对圣训的重视也就理所当然。
-
这里专门记述艾哈迈德·爱敏与部分学者的学术对话,让读者一睹客观、冷静,不冲动、不做作的对话范例,我们多么需要从中学到远离诡辩、崇尚真理的风格。
-
必须指出:这些改革家所面临的“疾病”至今未得到有效的治疗;穆斯林群体依然饱受这些疾病的困扰,坐卧不宁。渴求重返辉煌的青年们,仍然对这些疾病有着切肤之痛,却束手无策。读到这些改革家克服重重困难,提供医病良方,付出艰辛努力,驱除屈辱和衰败,青年们就会以他们为榜样,汲取他们的指导性理论,致力完成他们未竟的改革事业。本书明快的叙事风格,真诚的改革情感,吸引着读者去享受它的文字,犹如在读每个改革家的故事而不是传记。如果作者成功吸引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去读他的这部作品,那么作者的目标已经实现。
-
在中国西北,许多穆斯林把热哲布月称作“头月份”,认为在这个月封斋是最贵的,而且说在头三天封斋会得到封七百五十年斋的回赐;有些人还说这个月有专门的拜功,等等。那么,热哲布月果真有专门的斋戒和专门的拜功吗?
-
潜心观察、研究穆斯林生活规律的人不难发现:科学在他们的生活中不是以一种理论的形式出现,而是一种流动的生活;科学在穆斯林那里不是仅仅为一些科学家和文人们所张扬的一种理论,而是虽目不识丁的文盲、普通老百姓也自觉遵守的一种“生活习俗”。
-
如果说,我们拥有巍峨的清真寺,成群的礼拜者,那么,我们更应该拥有杰出的思想家,无畏的战士。因为我们不要忘了,当年在枣树和土墙围就的“拜殿”里,穆圣培养了人间的“天使”,世界的征服者,文明的传播者。
-
作为思想家,格尔达威对西方文化给予批评的同时,并没有掩饰穆斯林本身所存在的病症,而是给予不客气的批判。他指出,穆斯林中确实有一些人向人们提供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伊斯兰”,他们所提供的“伊斯兰”信仰中提倡宿命论,功课中提倡形式主义,思维中提倡肤浅和庸俗,行为中提倡消极和悲观,古兰经注解中提倡字面和教条,法学中提倡表面化,生活中提倡外观化。